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对中国的研究非常丰富,著作颇丰,作品包括《天安门》《追寻现代中国》《曹寅与康熙》等。
黄山 龙周园 | 文
今年78岁的史景迁是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家,专攻中国近现代史及东西方关系的研究。他的史学著作以叙事见长,考证严密,深入浅出。他最畅销的作品《追寻现代中国》,以生动的笔触,从明末一直写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日前,财新记者专访史景迁,请他谈谈历史与现在的中国。
财新记者:让我们从你最具代表性的书《追寻现代中国》谈起,这本书出版于24年前。在书中,你提到通过回顾明末以及清代的历史,我们能深刻地理解目前中国在争取自己在世界中地位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这本书出版24年后,你对当今中国有什么新看法?
史景迁: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书中已经有一些大方向的判断,这些观点准确与否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在更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中,人们通常认为,明朝或乾隆时代政治制度的衰败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所以当时讲述中国历史的方式就是:制度的瓦解,接着是更加剧烈的瓦解、戏剧性的变化,以及国家资源彻底地调整和再分配。但我在耶鲁大学教授入门课的时候就想过,如果从一个更强盛的中国开始讲起,会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尽管期间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和战乱,如果以一个强盛的中国作为开端,我的学生以及公众对那段弱势的历史时期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段弱势的历史就不再是一个漫长、持续不断的过程,而是一段更短的过程,且充满着变化和发展。
我一直小心翼翼,不想大而化之地概括中国历史,因为这超出了我的知识领域,中国是如此之大。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新版《追寻现代中国》前不久在美国发行,这已经是第三版了,而且它已经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将来这个作品能不能站得住脚还很难说,但我希望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财新记者:在你的很多著作中,都贯穿着西方文化和科技对中国的影响。你认为这种影响今天还有多大的重要性?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史景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历史阶段时,背负着巨大的遗产:一方面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是与外国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时,这些关系很鼓舞人心。
我学生时代写的第一本书名叫《改变中国》,主要内容是观察西方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被用来分析明代以来的中国。
本来我是做好准备接受这种分析方法。似乎对我来说,这是历史自然而然地呈现自己的方式。后来问题来了,为什么事情会变糟糕?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为何会恶化?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中国帝国制度的自身弱点、内在压力,以及中国人对西方一系列苛刻的要求做了很多妥协:也就是我们说的“通商口岸体系”。开埠限制了中国发展和利用自有资源,并将对资源的控制权让渡给了外国人。这最后变得不可接受。

财新记者:你的作品文字优美,且见微知著。在你笔下,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个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跃然纸上:既有西方人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生涯、康熙皇帝的统治之术及其内心世界,也不乏清初农村百姓贫苦的生活境况。你很擅长用讲故事、个人史的方式来写中国历史。如果今天你再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谁会成为故事的主角?
史景迁:我这次在北大做第一个演讲时,脑子里浮现的都是第一个游历欧洲的中国人——沈福宗。对于他,我们掌握了扎实的史料信息。他是南京人,也是一名天主教徒。
有记载显示,大约在1687年,沈福宗到达欧洲并去了巴黎、罗马和伦敦,最后还去了牛津大学。在这一段时期,他用一些时间完成了宗教使命,更多的时间他都在从事我们说的“文化外交”。他见了一些英国科学家,也和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进行了会面。英国国王对中国很感兴趣,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沈福宗与法国国王进行了会面。
我对这个人物很感兴趣。研究他,就是在研究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的变通性。它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让中国显得不再那么一成不变,而是更灵活变通。这一切都是因为一种国际语言——拉丁语,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的天主教徒和西方文人都掌握了拉丁语,这让沈福宗到了英国后,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跟英国的专家、科学家以及官员交流,并且能在牛津大学开展编书工作。
本来这可以成为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因为康熙皇帝对外国感兴趣是出了名的,他可能也听说了沈福宗游历欧洲的故事。但可惜的是,沈福宗在离开英国后不幸死于热病,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疾病,这是个巨大的遗憾。所以,这样一段本来可以成为重大文化交流的事件,最后只能存在于人们对历史的好奇之中。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目前我有一部分时间在做关于沈福宗的研究。
财新记者:现在官方对中国当代史的叙述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人们一说到中国历史,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谈起。你怎么看官方对当代史的叙述?
史景迁:鸦片战争或许受到了过多不必要的关注,不过这对于现在的争论也是有帮助的。在19世纪40年代,对于鸦片贸易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它,当时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存在分歧的。有些中国人,包括一位朝廷高官,认为或许应该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因为这样政府才能够进行监管、征税并从中获取收益,而不是让所有的收入都流入外国商人的口袋里。这又把问题带入极度复杂的历史讨论当中。
但话又说回来,所谓的“官方叙述”取决于是哪些历史学家在写作什么题材,以及谁在支持他们。是只有商业市场在发挥作用吗?是一个普通的出版市场,在没有官方指令的情况下正常运作的吗?同时,也许现在中国需要更开放的讨论空间。
财新记者:同样是汉学家,你那一代和现在这一代之间,有着怎样明显的不同?
史景迁: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并不视自己为一个汉学家。在我看来,汉学的研究范畴包括古汉语、古代文本的传统,以及儒学和更早时期各种学术流派的相关知识。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领域。直到最近,其实都没有多少汉学家。
尤其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中国研究真的还处在我所称之为“大冷战理论”的背景之下。苏联和中国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点当时也就这样被学界接受。对于中国历史进行政治化的解读,这一观念当时在这个领域根深蒂固,这个领域的很多学者也深受其影响。
对于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来说,判断中国的发展走向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所获得的信息常常是非常不准确的,或是非常极端化。现在研究中国的学者持有的见解千差万别,既有喜欢中国的,也有担心甚至害怕中国的。但他们是一群非常出色的学者。
因此,从知识的角度来说,中国研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我觉得这非常棒,也理应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小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同时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语言方面也很在行。所以,如果沈福宗能来到现代,也许中西之间会有新的共同语言,这种环境也为中西方更具开放性的交流提供了新机遇。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不仅对于西方,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作者为财新记者。记者林栋、Gus McCubbing对此文亦有贡献)
-----------
○ 关注“旁观中国”微信公众号“on_china”,或扫描下图二维码,获得每日完整版推送。我们为您精选全球舆论对中国话题的报道、分析和评论,发掘“吐槽”与深意。
○ 联系我们:博客:旁观中国;新浪微博:旁观中国OnChina;腾讯微博:旁观中国
○ 欢迎发来评论或文章推荐,可直接发微信,或邮件至:onchina@caixi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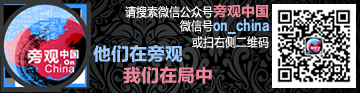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